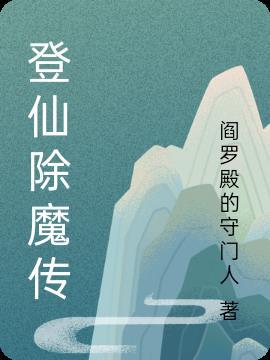小燕文学>水浒传之林黛玉倒拔垂杨柳 > 第13章 番外武松视角老少恋上 new(第2页)
第13章 番外武松视角老少恋上 new(第2页)
什么白鲦鱼和板刀面,是他们之间的暗号吗?
白鲦鱼挺好理解,是浪里白跳的谐音吧,板刀面是指张横吗?
是说张横长得像面?
我怎么看不出来?
武松一头雾水。
林黛玉也很疑惑:“二哥哥,什么呆呢?”似乎是在笑话他。
她这个又爱笑又爱哭的脾气真是改不了啊。
唉,怎么可以这么灵动,这么青春飞扬呢?
换作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每天嘻嘻又呜呜的,多少有点可怕。
如此鲜亮的生命力是少年的特权,而她可以永远手握特权,永远潇洒,永远活跃,哪怕有一天他都八十岁了,她依然……再一次,武松感到自己的脉搏开始兴奋地鼓动了。
下午,水寨,林黛玉在赏荷,他又一次在后边满脸杀气地盯着。
张顺忽然出现在他后面:“兄弟,你怎么在这?从山前到这里还是挺远的,没想到你这么有兴致。你眼神凶巴巴的在看什么呢?”
武松说:“看林教头。”
“你消息还挺灵通的,林教头今下午带着妹妹来水寨了,一起过去吗?”
“不。看某个人不顺眼。”
“为什么?她完全是个挑不出毛病的大家闺秀!”
张顺还挺聪明的,知道他是指女方,没有误解成讨厌林教头。武松思忖片刻,回答道:“头太长了。”
“你是指头长见识短么?这种说法不能当真,公孙道长每天披头散的,谁敢说他没见识。”
也对。武松换了个说法:“头太多了。”
“身体肤受之父母,证明她被爱护着,我羡慕还来不及。”
唉,收回前话,张顺有时候也挺笨的,怎么就听不出话外音呢?虽然张顺人很好,但武松还是得出了一个结论:跟张顺尿不到一个壶里。
忽然,不知从哪儿射过来白光,跟宝剑似的,直冲冲地朝他的眼睛刺来,一个闪动之间就命中了他。
他烦躁得想打人了。
他试图用袖子把亮光扫开,谁知每挥动一下手臂,那光便刺一下,令他收紧的牙关呲呲痒。
定睛一看,原来是林黛玉的头,在阳光下绽放出钻石般的光泽。
斑驳的阳光像一群调皮的小鱼,在少女胜过明镜的肌肤上游泳。
那水汪汪的、金灿灿的模样,几乎要胜过一头有人性的母牛的眼神。
走到树阴叶翳处,鱼儿们又忽地扑通一下,好似逐渐融化的酥酪般潜到水底去,只在空气中余下隐约的甘甜,便不再冒头了。
啊,对了,武松又想起来一个故事:林黛玉的头厚得半点缝都看不到,如果是因为所梳型不得不显露出一溜白路,她会想办法用饰品或者鲜花遮住,总而言之,绝对不能让缝出现。
唉,她真的很聪明,很热爱生活啊。怎么总是在一些细节处现她的可爱呢?再一次,他烦躁得想打人了。
这时候,老天准备犒劳他瞪得疲惫的眼睛,安排她在这烦躁的关节时回转身,让那身姿和脸蛋暂且出现在他的视野里,给干燥的眼睛施舍一点带着酸臭味的热水。
路过石阶时,湿润光洁的苔面令她脚步踩滑,倾倒在地。
可怜的小女孩,山路不会根据她的体质去修建,只能她去适应,这一摔不知道又要在床上躺多久。
只有他看到了,当她倒地时,那对挺翘的胸在跳。
走在回山关的路上,想起那对似蹙非蹙的眉毛,想起那双可以把湖水都烧干的黑眼睛,还有那对活泼美丽的胸乳,他感到自己像一条口吐白沫的狗一样窒息、抽搐,随时都可能癫。
一个危险的想法开始萌生。
野性的渴求和人性的怯懦接替着掌控他的情绪,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肉体与灵魂争相嘶鸣的感觉,让他一刻都不能稳定,仿佛有一只啄木鸟在心室里捣蒜般地叼啄着,把他的心脏都啄成了一块稀烂的咸鱼干。
关于那双黑眼睛的印象,那头厚得累脖子的长,那对……一颗小石子悄悄躲入鞋中,只需要安安静静地躺在脚底,就能不停地折磨他。
他不敢确定,这就是欲望吗?
这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,他原本以为欲望只会集中于下体,无非是生殖器抬头又沉寂的一段过程,每天早上都会有的,无视老二就行了,他的大脑肯定还是清醒的,动作也是轻松自由的,因为人类的上下半身之间有不可逾越的代沟。
勃起并不代表他喜欢女色,有生理反应也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。
他是这么看待欲望的。
而事实上,欲望是当看到那个女人时,体内会突然咚的一下,身体核心猛然开始奏响猫科动物似的呼噜声,在那滚烫的肌肤之下,腹部不断传来沉重的坠落感,似乎器官和血液都在往外翻涌,然后逐步产生失重似的真空的错觉。
这种感觉是全身性的,压倒性的,狂热性的,遍布每一个细胞,将人彻底包裹,无处可避。
而这一切,只是因为她不小心踩滑了,只是因为她的乳房跳了一下,只是因为她在意识到出糗后做了个害羞的动作……只是这么一下,就多么令人恐惧,多么令人惊惶!
害他显些以为是得了精神失常,是癫痫病。
武松神志恍惚。
当他一如既往地站在梁山泊的土地上时,觉得自己就像高烧后不断谵语的病人,整天都浑浑噩噩,仿佛毒日下晒得汗流浃背还要一言不地派兵列阵的人不是喽啰,而是他自己,仿佛路过石阶时被昨夜雨水所戏弄的人不是林黛玉,而是他自己。